目录
快速导航-

如初见 | 白马
如初见 | 白马
-
晨读本 | 读者与作家
晨读本 | 读者与作家
-
晨读本 | 秋冬
晨读本 | 秋冬
-
晨读本 | 认真工作
晨读本 | 认真工作
-
晨读本 | 白鹭与稻子
晨读本 | 白鹭与稻子
-
晨读本 | 因为有月亮
晨读本 | 因为有月亮
-
晨读本 | 除夜作
晨读本 | 除夜作
-

万物生 | 少年的你
万物生 | 少年的你
-

万物生 | 听风
万物生 | 听风
-

万物生 | 心态
万物生 | 心态
-

万物生 | 用温度战胜对手
万物生 | 用温度战胜对手
-

万物生 | 大事不着急
万物生 | 大事不着急
-

笔生花 | 美丽的嘉荫
笔生花 | 美丽的嘉荫
-

笔生花 | 万里和万卷
笔生花 | 万里和万卷
-

笔生花 | 花鸟昆虫创造的奇境
笔生花 | 花鸟昆虫创造的奇境
-

笔生花 | 故乡的春节
笔生花 | 故乡的春节
-

锦年华 | 做自己前先寻找自己
锦年华 | 做自己前先寻找自己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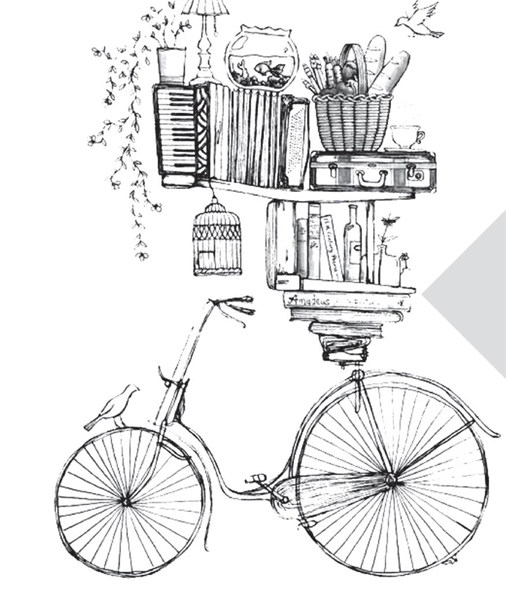
锦年华 | 买书
锦年华 | 买书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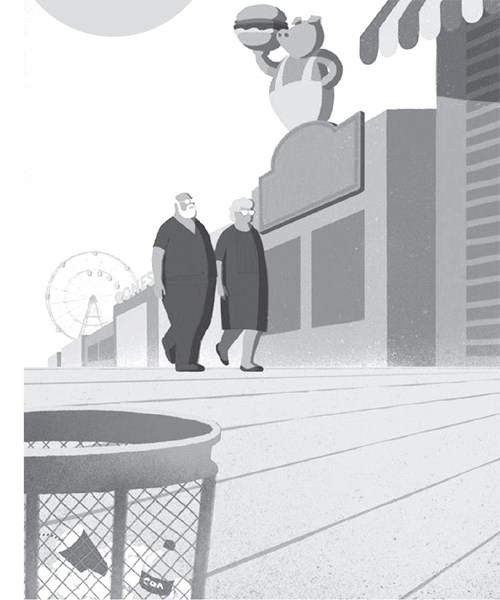
全世爱 | 我外公外婆的倾国之恋
全世爱 | 我外公外婆的倾国之恋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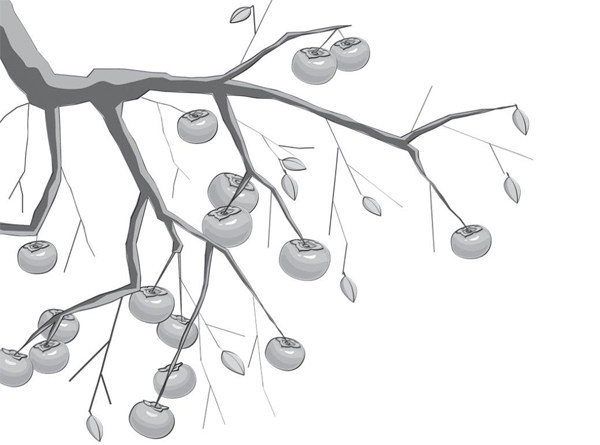
全世爱 | 很多东西长着长着就像凹村的人了
全世爱 | 很多东西长着长着就像凹村的人了
-

全世爱 | 母亲常制的九种面食
全世爱 | 母亲常制的九种面食
-

全世爱 | 他看见了我的眼睛
全世爱 | 他看见了我的眼睛
-

想象力 | 世界上最后一个机器人
想象力 | 世界上最后一个机器人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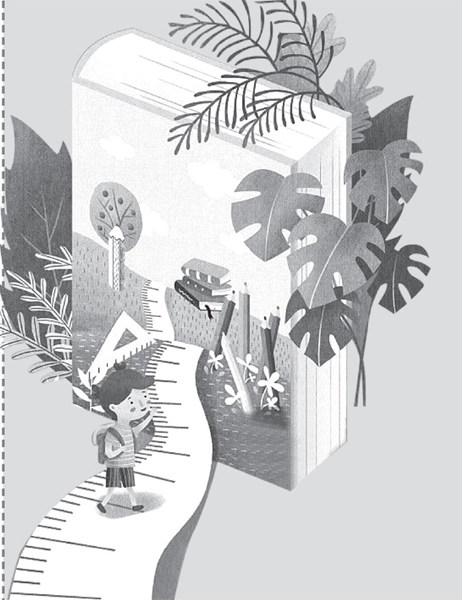
想象力 | 叶子书,只有一页
想象力 | 叶子书,只有一页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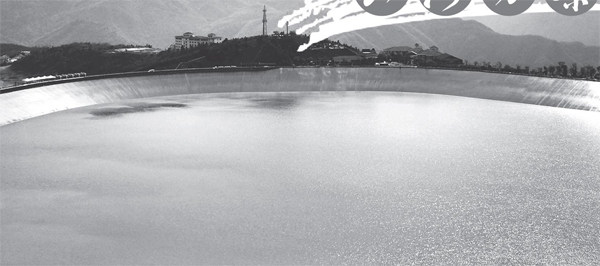
想象力 | 山河万朵
想象力 | 山河万朵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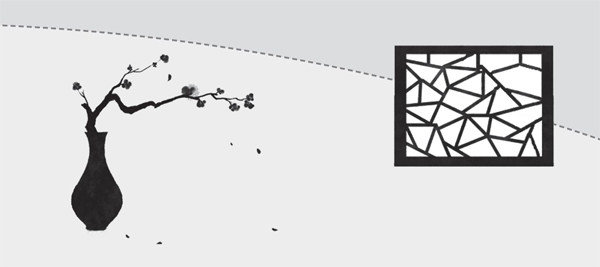
美如画 | 留将一面与梅花
美如画 | 留将一面与梅花
-

美如画 | 萤火一万年
美如画 | 萤火一万年
-

美如画 | 月影
美如画 | 月影
-

美如画 | 农具在时间深处闪光
美如画 | 农具在时间深处闪光
-

倾阅读 | 47号塔上的男人
倾阅读 | 47号塔上的男人
-

倾阅读 | 三代人书房的变迁
倾阅读 | 三代人书房的变迁
-

倾阅读 | 舌尖上的世界
倾阅读 | 舌尖上的世界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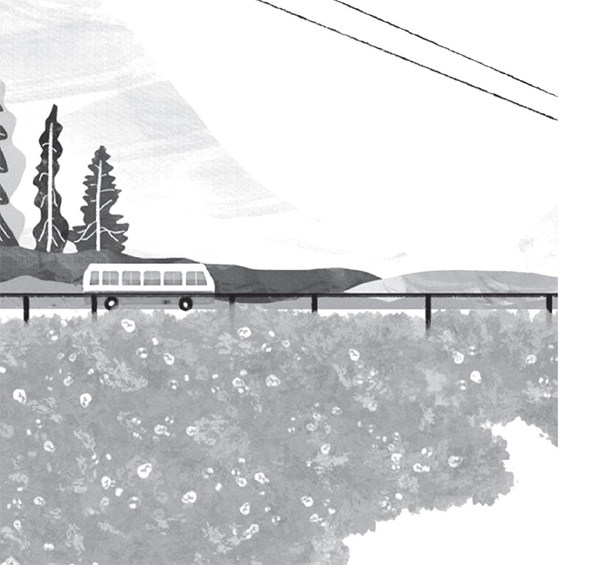
倾阅读 |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,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
倾阅读 |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,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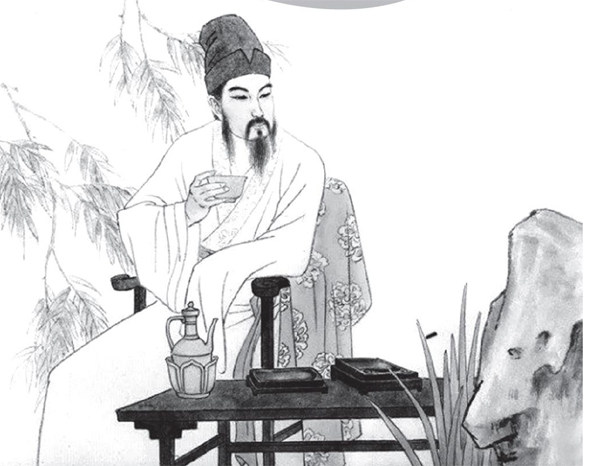
倾阅读 | 有个旷古绝今的大才子哥哥是什么感受
倾阅读 | 有个旷古绝今的大才子哥哥是什么感受
-

倾阅读 | 叶叶欢歌
倾阅读 | 叶叶欢歌
-

倾阅读 | 我的两个梦
倾阅读 | 我的两个梦
-

倾阅读 | 月亮在叫
倾阅读 | 月亮在叫
-

星星诗 | 彝人谈火
星星诗 | 彝人谈火
-
星星诗 | 阅读
星星诗 | 阅读
-
星星诗 | 幸福
星星诗 | 幸福
-
星星诗 | 幸会,以诗之名
星星诗 | 幸会,以诗之名
-
写作课 | 写作一点也不难
写作课 | 写作一点也不难
-
读书会 | 革命理想高于天
读书会 | 革命理想高于天
-
读书会 | 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魅力何在
读书会 | 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魅力何在
-
读书会 | 趣贴
读书会 | 趣贴
-
读书会 | 海伦·斯诺续写《西行漫记》
读书会 | 海伦·斯诺续写《西行漫记》
-
先生说 | 黄生借书说
先生说 | 黄生借书说
-
先生说 | 谈生命
先生说 | 谈生命
-
先生说 | 读书要分两步走
先生说 | 读书要分两步走
-
上镜吧 | 雾
上镜吧 | 雾
-
上镜吧 | 过路客
上镜吧 | 过路客
-
上镜吧 | 心中是春,花香自来
上镜吧 | 心中是春,花香自来
-
上镜吧 | 八九十枝花
上镜吧 | 八九十枝花
-
上镜吧 | 春天,花开得那么好
上镜吧 | 春天,花开得那么好
-
互动吧 | 浮生只合尊前老,雪满长安道
互动吧 | 浮生只合尊前老,雪满长安道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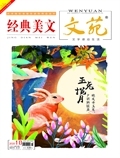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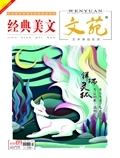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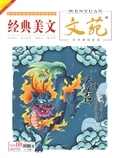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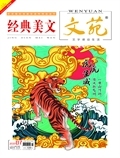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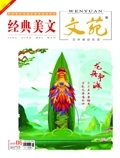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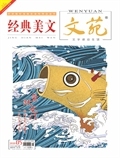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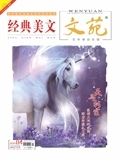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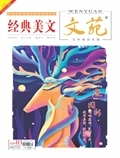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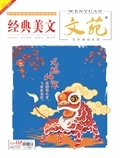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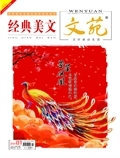








 登录
登录